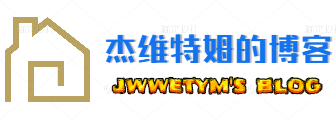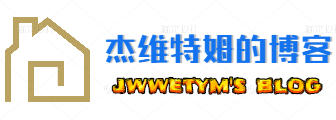黄纯武妇科崩漏
瘀结血崩(子宫肌瘤)1例
陈某某,女,47岁,初诊:1983年10月20日。
月经过多10余年,近1年加重,每次用纸4~5刀,色黯红有大血块,经行腰隐痛,周期25~27天一潮,经行8~9天干净,末次月经10月14日来潮,现仍未干净,素头昏、两腿软,纳差,心慌,口干喜饮,烦躁多汗,大便干结,小便黄。今年6月妇检:子宫鸭蛋大,质稍硬,诊断“子宫肌瘤”,作B超结果相同。舌质黯淡,苔薄,脉细。
此郁结血崩。治宜:软坚化结,调经止血。
夏枯草15g 益母草20g 浙贝母15g 生牡蛎30g 鳖甲20g 白芍15g 山药15g 冬瓜仁15g 枸杞子15g 三七5.5g
二诊:1983年11月25日。
服药后月经于11月10日来潮,血块减少,经量亦减少,仅用纸3刀,大便正常,余症减轻。
继服上方。
服上药加减半年。妇检:子宫稍大,B超未发现异常,月经量基本恢复正常。
按:“子宫肌瘤”属中医学癥瘕范畴,由经行之时,血欲出之际,停于胞宫,经血蕴积,煎熬成瘀,瘀血占据血室,致血不归经而崩。瘀血日久化热化火,又经崩阴血大伤,阴虚生内热,热灼冲任,迫血妄行,故崩漏并见烦躁多汗,口干喜饮,便结,尿黄,其头昏、心慌、腿软,乃失血过多,血虚失养所致。可见阴虚瘀热是此病发生之重要机理,故治宜化瘀养阴,清热止崩。方用夏枯草气寒而味辛,凡结得辛则散,气寒清热,兼通血脉凝滞之气,有软坚散结之功;浙贝母性寒,功能开郁散结、解毒化瘀;鳖甲咸平,补阴气、潜肝阳、消癥瘕,缪希雍《本草经疏》谓其“润下作咸,甲主消散者,以其味兼平,平亦辛也,咸能软坚,辛能走散,故《神农本草经》主癥瘕坚积”;生牡蛎咸涩性凉,能软坚散结且有收涩固脱之功。重用益母草活血调经,三七末既能化瘀血,又善止血妄行,乃理血妙品;用白芍养肝血,山药补脾阴,枸杞子补肾、养冲任。此方组成,虽下血如崩,但不止血,血不归经,徒止何益?虽有癥瘕但不攻破,亦不用辛温助动之药,而重在软坚散结,不失通因通用之意;其软坚散结之药,亦选鳖甲滋阴而软坚,牡蛎软坚而固涩,夏枯草、浙贝母软坚而清热解毒,三药同用使阴血得充,虚火得清,使离经之瘀结尽化其滞,未离经之血永安其宅。用山药、枸杞子、白芍养肝脾肾三脏阴血,补阴而无浮动之虑,循血而无寒凉之苦。即便活血亦选用能止能化之佳品,如三七、益母草之类。
气虚血崩1例
杨某某,女,49岁,初诊:1984年9月18日。
月经先期、量多3年余,开始服中西药可以止血,近年月经量越来越多,出血时间长,服中药亦不能止血。末次月经8月25日来潮,至今已20余天仍未干净,开始几天量多,有大血块,但腹痛不明显,每天用1刀多纸,后量减少,但淋漓不尽。近来感冒,不适,有冷感,欲呕,口干喜热饮,大便干结,小便可,面色萎黄,B超提示“子宫肌瘤待排”,舌质淡,苔薄白,脉细。观前所用中药均系清热凉血、固涩止血之品。
此气虚血脱。治拟:补脾益气,佐化瘀止血。
黄芪15g 白术10g 黑姜炭3g 甘草6g 三七末4.5g 制首乌15g 莲房炭15g 白芍15g 蒲黄炭10g
二诊:1984年9月26日。
服上方4剂阴道出血停止,大便正常,胃中冷感减轻,仍口干喜热饮,下腹部有点作胀,心慌,头昏,乏力,舌淡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加橘红6g。
三诊:1984年10月15日。
这次月经于9月30日来潮,量减少,用纸2刀,7天干净,大血块明显减少,下腹胀消失,余症均减轻,饮食增加,精神好转。
继服上方。
随访3个月,月经正常。
按:崩漏日久致阴血流失,气随血耗因之而虚,加上长期投以寒凉阻碍阳气升发,又犯见血止血之诫,介类、胶、炭之属,酸敛滋腻用之不慎,终碍脾胃。傅青主早就告诫曰:“世人一见血崩,往往用止涩之品,虽亦能取效于一时,恐随止随发,继致终年累月不能全愈者有之。”患者服止涩寒凉太过,虽止血一时,但损伤脾胃阳气,致胃冷欲呕,口干喜热饮,医者只知火盛动血,一见口干便结,以为热证无疑,不知便结固有热燥大肠,亦有血枯不润;口干既有热灼津液,亦有阳虚津液不能上承,辨证要点是喜热饮还是喜冷饮;结合其舌淡,苔薄,面色萎黄,喜热饮,属脾虚可见。脾者生血、统血,今患者头昏心慌,脾虚不能生血,崩中漏下不止,脾不统血使然。血者阴类,其运在阳,脾阳大虚故血无所统,所谓“阴虚阳必走”是也。《类证治裁》曰:“气虚血脱,宜温补摄之”。方中以黄芪为君,味甘性温质轻而润,能入脾补气,《本草求真》谓其“为补气诸药之最”,补气摄血是也。赵献可曰:“古人治血,必先理气,气药多血药少使阳升阴也,有形之血大脱不能速生,几微之气惟以无形生有形,以阳气之药维之阴血暴亡之后,此阴阳相维之妙。”滋以白术健脾益气助其生发之气。黑姜温中散寒,《本经逢原》谓其“禀阳气之正,用治里寒”,止而不移,炒黑去其辛散之性,而有止血、引血归经之妙,傅青主曰:“黑姜引血归经是补中而有收敛之妙”。莲房炭苦涩温,止血,《本经逢原》谓其“功专止血,故血崩下血溺血,皆火烧灰用之”。白芍敛阴,配甘草酸甘化阴,补阴血之不足;制首乌润肠通便,制后去毒,留润肠之功,而去滑利太过之弊。患者检查疑是子宫肌瘤,虽无腹痛,但大血块多,可见瘀血有之,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曰:“瘀结占据血室,而致血不归经”。温中散寒止血,对脾虚不统血自属正治,但对瘀血却非其治也,故佐三七、蒲黄炭,三七善化瘀血又善止血妄行,为理血妙品,蒲黄活血化瘀炒炭又有止血之用。二药均一走一守合于一体,止血而化瘀,塞流而不碍畅流之义,使瘀化血活,结开畅流,血行经络以止经漏。观全方不求止血而血自止,温之止之,行之止之,与世俗见血非投凉即滋阴,相互成风不重辨证,绝然有异。
阴虚血崩1例
胡某某,女,42岁,初诊:1983年5月25日。
自去年3~4月份起月经量开始增多,9~10月份逐步经期提前,20余天一潮。今年月经紊乱,4月份停经47天后月经来潮,开始大出血有大血块,当时诊刮,根据病检报告诊断为“子宫内膜增殖症”,诊刮后出血仍未干净,服避孕药及安宫黄体酮,血仍未止,做B超提示“子宫肌瘤待排”。现患者阴道有少许出血,伴烦躁、口干口苦、小便黄、头昏,舌尖红,苔黄,脉细数。
此肾虚火旺,迫血妄行。治宜:滋肾养阴,固肾调经。
地骨皮12g 旱莲草24g 生熟地各30g 阿胶15g 白芍15g 麦冬15g 五味子4.5g 生牡蛎30g 益母草10g 。
二诊:1983年6月5日。
服药后6月1日出血干净,精神好转,但仍头昏,小腹痛,肛门下坠,前几天患泌尿系感染,服西药3天好转,余证均有减轻。舌质红,苔薄,脉细数。
继服上方加甘草6g、黄柏10g。
三诊:1983年7月7日。
末次月经6月29日来潮,头两天量多,用纸1刀+,后两天量减少,7月6日干净,经行7天,用纸近3刀,无腹痛,但仍感头昏。舌质淡红,苔薄,脉细。
上方加太子参15g。
四诊:1983年7月28日。
这次月经7月25日来潮,已用纸一刀半,今天量不多,无明显不适,舌质正常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,加贯众炭10g。
观察至11月份,患者月经正常,27~28天一个周期,用纸2刀,精神好转。
按:经所曰“阴虚阳搏谓之崩”,是言阴虚而阳盛始发崩中。阳主气火,阴本涵阳,今阴不足,则阳独盛,迫血妄行而成崩中。《血证论》指出血证“气盛火旺者十居八九”,“血与火原一家”,“血病即火病,泻火即止血”等等,无非是言“人莫不谓,火盛动血也”。患者崩漏兼见月经先期,烦躁、口干苦、舌红、苔黄,脉细数,属热证无疑,然此火非实火乃虚火耳。患者素月经量多,又大出血,气随血耗、阴血大损,阳气亦因之而势微,可见此火非阳之有余,实阴之不足。阴虚何脏,烦者心也,躁者肾也,口苦尿黄肝也,又经本于肾,肾者水脏,主五液,今肾水不足不能镇守胞络相火,故血走而崩。方中重用生熟地大壮肾水,养肾精兼泻肾火,助以阿胶之甘大补精血,补不足之阴以配阳,泻有余之火以护阴,收水升火降之功。麦冬养心阴、清心火,白芍养阴敛肝,地骨皮清至里之热、降浮越之火,旱莲草性凉最善止血。妙在用五味子固肾摄精,助以生牡蛎其质类金石,性善收敛;肾者封藏之本,藏精气而不泻,今肾精亏损,固摄失职,只滋阴养血,势必血难以生,阴难以充,必加固涩之品以收敛耗散之肾气,始为正治。其中生牡蛎又能散结软坚化痰治子宫肌瘤,使血之已离经者尽化其滞,血之未离经者永安其宅。血以和为贵,经以调为顺,故佐益母草调经,祛瘀生新。全方妙在全不去止血而惟补血,又不止补血而更补阴,非惟补阴而更固肾,俟阴复而血复,血复而火灭,火灭而血自止。虽言热迫血行,但不用苦寒折火,而甘寒柔润重养肝肾,以清冲任之热,辅以固肾调经之品,补阴而无浮动之虑,缩血而无寒凉之苦,以清凉之中不离止涩,而止涩之中又须和血调经使其畅流,乃治阴虚火旺迫血妄行之崩中之一般法则。
心肾不交血崩1例
陈某某,女,30岁,初诊:1984年8月26日。
近一年半,月经过多,过频,有时一月二潮,持续7~15天,月经量多、色红。每经潮前几天量多如崩,后则淋漓不尽,月经周期提前,末次月经1984年8月9日至今仍淋漓不尽。口臭,多梦,平时经常牙龈出血,阵发性心慌,舌上有较深的裂纹,苔薄白,脉有间歇。
此乃心肾不交。治拟:滋肾水,清心火。
生熟地各30g 柏子仁10g 麦冬15g 五味子6g 旱莲草30g 阿胶10g 莲子心6g 桑椹子15g 白芍15g 甘草6g 沙参15g
二诊:1984年8月30日。
服药后第一天阴道反有淡黄色稀水,第二天出血止,近两天感胸闷、喘气、牙出血,身烦躁,心慌有所好转。舌淡,苔薄白,舌中有裂纹,脉有间歇。
继服上方加青盐1g。
三诊:1984年9月14日。
服上药20余剂,感觉全身轻松,精神好转,末次月经9月10日来潮,量中等,色红,现已干净,口臭,牙龈出血已好转,饮食增加,舌中裂纹变浅,脉细。
继服上方加乌梅10g。服药20余剂月经自调,衄血停止。
按:患者月经不调年余,量多,持续时间长,现出血已半月余仍淋漓不止,《妇人规》指出:“崩漏不止,经乱之甚者也”。冲任损伤,不能制约经血,是崩漏之症发生的主要机理,然引起冲任损伤的原因有热、有瘀、有虚。《素问•阴阳别论》谓:“阴虚阳搏谓之崩”,是言阴虚而阳盛;盖阴主精血,阳主气火,阴本涵阳,今阴不足而阳独盛,迫血妄行而成崩中。《傅青主女科》亦言“人莫不谓火盛动血也”,大出血或长期失血,气随血耗,阴血大伤,阳气亦因之而微,故“此火非实火,乃虚火耳”。患者长期出血,形体消瘦,阴血必虚,月经超前,量多,色红,口臭,热象即可概见。肾虚则经行量多,下血不止,水亏火旺则牙龈出血,舌乃心之苗,心火旺故舌上裂纹,心主血脉,心血不足则阵发心慌。病在心肾二脏,根在肾水不足,故治宜滋肾水兼降心火。方中用生熟地、旱莲草、桑椹滋肾清热止血,用熟地、桑椹、阿胶重在养精血,麦冬、五味子、沙参养心阴,柏子仁益心气,莲子心清心火。交通心肾之主方黄连阿胶汤以黄连、阿胶为主药,患者口臭、舌上裂纹、多梦可知心胃火旺,本应用黄连,但患者脉结代,黄连苦寒虽能清心胃之火,但有伐心气之弊,故改用莲子心作用平和,既清心火,又无苦寒太过之弊。药后阴道出血停止,但仍牙龈出血,烦躁,烦属心,躁属肾,病仍在心肾,肾水不足,虚火上浮,仅加青盐1g引火归源。
情伤血崩1例
汪某某,女,44岁,初诊:1983年4月7日。
去年元月份正值经期,爱人病逝,事后又与家庭发生纠纷,当时闭经三月余,其间感口苦胸闷,心下痛,低烧,大便干结,全身不适,人亦消瘦。后月经来潮量多,淋漓不尽,有时20余天不干净,经常头昏、心慌、烦躁、纳差,曾服用一些中成药、西药均未见明显好转,末次月经3月14日来潮,至今已20余天仍未干净,先量少,后逐渐量多,色黯红有块;白带不多,无明显气味。曾大生三胎,人流二胎。舌质红,苔薄欠润,脉弦细。
此肝郁气滞化火伤阴。治宜疏肝养肝,滋阴清火。
竹柴胡6g 荆芥炭4.5g 当归10g 白芍20g 生熟地30g 阿胶15g 山药15g 旱莲草30g 甘草6g 太子参15g 麦冬15g 五味子6g
二诊:1983年5月18日。
服药两剂,月经于4月9日干净,这次月经5月4日来潮,5月7日干净,经行3天,色红,用纸1刀,胸闷明显好转,已无低热,感头昏,大便干结,舌正常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加制首乌15g。
三诊:1983年6月10日。
服药后近两个月,月经已恢复正常,心情好转,大小便正常,时感腰酸痛,舌脉同上。
继服上方加桑寄生12g。
按:经水者,阴血也,冲任主之,藏于肝,通于肾。肝主疏泄,疏理血脉,宣泄气机,疏泄有节,气血通调,经自畅矣。肾藏精系胞,傅青主曰:“经本于肾”,肾精充足,肝体得养,冲任得荫益,血海宁静,封藏有制,经候如常。今正值经期,突受意外刺激,情志所伤,肝首当其冲,肝者将军之官,女子多愁善感,气机易郁,血脉易滞,疏泄失司则闭经、崩漏、胸闷、全身不适。五志过极,皆能化火,下灼肾水,上生心火则口苦、烦躁、心慌、头晕,大便干结。又经行日久,耗伤精血,阴血下虚,气无所附,横逆而散窜,终致肾无所藏。今患者出血20余天未净,张洁古曰:“……肝为血府,伤则不藏血,而为崩中漏下”,即由肝郁所致,治宜平肝开郁,郁解则木自达,肝舒则火自平,木达火平,血自归经而得藏矣。然木赖水养,滋肝必壮水,水足则木茂。方用竹柴胡、荆芥炭疏肝气,郁病皆因气不流畅,当以顺气为先,然理气之药多俱香燥之性,频服香燥,耗血伤精,故宜少少与之。荆芥炒炭后去其香燥之性,且有引血归经之功;又助以当归、白芍养肝血,肝乃藏血之脏,血燥则肝苦急,血足则刚燥之性平;用生熟地、阿胶、旱莲草滋肾壮水,子母同治;麦冬养心阴以通肝络;太子参、山药健脾益气阴,免于横逆之虑;妙在用五味子不但收敛为功,坚固心肾,且味酸入肝,肝欲酸,酸补肝,一药而心肝肾三脏兼之。虽病由郁致,但治之不重在伐其有余,而重在培其不足;虽病在肝,但治之不尽治肝,而兼治子母,且培土以防其未然,此收效妙也。
少女血崩(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)2例
例之一
潘某某,女,14岁,初诊:1985年4月2日。
自去年9月份,月经初潮起,至今一年余阴道出血淋漓不干净,时而量多如注,时而漏下淋漓难尽,有时持续数月之久,有时一月仅干净几天又潮。这次月经于3月6日来潮,至今近一个月仍未干净,期间曾服止血药无效,家属拒绝用激素治疗,现已用纸6刀,色鲜红,量时多时少,无血块,无腹痛;平素大便干,头昏,腰痛,纳差,口不干,时心烦;追问病史,自幼爱好体育运动,月经来潮后亦未终止,后因长期出血才不得不停止,现每劳累后出血增多;形体消瘦,面色萎黄,舌质红,苔中心微腻,脉细数。
此脾肾亏虚,气血不足。治宜健脾益气,滋肾养精。
太子参15g 生熟地各30g 山药15g 旱莲草20g 甘草6g 阿胶15g 白芍15g 冬楂炭10g
二诊:1985年5月9日。
服药后月经于4月8日干净,这次月经于5月7日来潮,量多,经期大便溏,欲呕,心慌,乏力,舌稍红,苔薄,脉细数。
继服上方加半夏10g、荆芥炭4.5g。
三诊:1985年5月16日。
这次月经5月7日至5月15日,经行8天干净,用纸3刀+,经后头昏乏力、心慌、口干喜热饮、恶心感消失,二便正常,但仍纳差,舌质偏淡,苔薄,脉细数。
上方去姜半夏、荆芥炭、太子参,加党参15g、炒枣仁10g。
四诊:1985年7月14日。
这次月经于6月24日来潮,6天干净,用纸2刀余,无特殊不适,仅经后感头晕、乏力,舌质淡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,加山萸肉15g,生熟地改成熟地20g。
按:本例或血下如注,或淋漓不尽,交错出现,并见头昏、乏力、纳差、面色萎黄,可见脾胃虚弱,不能摄血归源使然。每动则加剧者,乃动而耗气伤精故也,又患者年方二七,肾精未实,肾气未充,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,古人有少女治肾之说,肾者主蜇,封藏之本,精之处也。青主曰:“经本于肾”,崩漏乃经乱之甚也,观其崩漏并见腰酸腿软,肾虚确有之。正如李梴曰:“脾胃有亏,下临于肾……迫血下漏”。从阴阳论之,长期出血阴分必亏,阴虚生热则舌红、脉数而烦,阳随阴泄,亦因之势微。虽年少之人火炽血热,毕竟崩漏日久,气血俱亏,既脾肾不足,气血俱虚,就应补益脾肾,益气养血。方用太子参、山药、生甘草补脾胃,一则益生发之气,使脾气升腾,血行经络,则无复崩矣;一则甘味药补气举世皆知,殊不知甘能生血,甘能养脏,此阴生阳长之理也。这里妙在补中气不用党参、白术、炙甘草,而易以太子参、山药、生甘草,以其补气而兼能益阴,味甘而无温燥之性。崩漏之症本动之有余,治必以静镇之,如用参术,益助其烈,更竭其阴,况患者舌红、脉细数,已有内热之象,治之稍有不慎,致祸甚速。又脾不健运,损及肾水,单补脾胃,不顾肾亏,终不尽病情。故用生熟地、白芍、旱莲草、阿胶养精血,阿胶、旱莲草又有止血之功。冬楂炭消肉食导滞,因其舌中心苔腻,炒炭又有止血之妙。血止后即将太子参、生熟地改党参、熟地,加山萸肉,补脾肾以固其本,补其虚。此时崩漏日久,阴精阳气随之大泄,所谓“贼去楼空”,患者虚惫,此时血止无虑,补气养阴用太子参、生地又力嫌不足,非党参、熟地不足为功。山萸肉强阴益精,涩精气。崩漏日久肾失封藏,固涩肾精尤为重要,又非补肾健脾等法所能代替。古人治崩有塞流、澄源、复旧三法,黄老治崩虽不尽用止法,亦不违背此旨,不重于止血,而重在澄源固本,又澄源固本不碍于止血,其用药精细即在于此。
例之二
梁某某,女,16岁,初诊:1985年6月19日。
月经13岁初潮,开始基本正常,14岁时因经期赛跑以及负重劳动即发生大出血,不能自止,曾多次住院治疗,经用中西药稍有好转,但经期、经量仍不易控制,有时一月两潮,有时整月不干净,非用激素方可止血,有时经净后复行,且量多如注,并伴心慌、纳差、口中乏味,长期便溏、头痛,舌质淡红,苔薄白,脉细数。
党参15g 黑姜炭3g 熟地20g 白术10g 山药15g 芡实15g 白芍15g 山萸肉15g 枸杞子15g 阿胶15g 补骨脂10g 荆芥炭4.5g
二诊:1985年7月10日。
服药后月经于7月5日来潮,量多,色红,有块,小腹痛,块下痛减,今日有将净之势,食纳二便尚可,苔薄白,脉细数。
太子参15g 熟地20g 旱莲草20g 阿胶15g 白术10g 山药15g 白芍15g 甘草6g 芡实15g 荆芥炭4.5g 枸杞子15g
三诊:1985年7月24日。
月经于7月12日干净,经净后未复行,头已不痛,但仍腹泻,腿软,口干喜饮,厌油荤,苔白,脉细。
上方去阿胶、桑叶加焦楂炭10g、炒扁豆12g。
四诊:1985年8月14日。
月经于8月6日来潮,6天干净,用纸一刀半,大便正常,舌淡红,苔薄,脉细数。
继服上方10日方去阿胶、荆芥炭加桑椹15g、鸡内金10g。
五诊:1985年9月20日。
上次月经8月26日来潮,又量多如崩,现月经已干净,呈贫血面容,苔薄白,脉虚数。
熟地20g 旱莲草20g 阿胶15g 白术15g 山药15g 白芍15g 甘草6g 芡实15g 枸杞子15g 党参15g 山萸肉15g 炒枣仁10g 黑姜炭3g 鸡内金10g
六诊:1985年12月23日。
服上方加减3月余,月经基本正常,末次月经12月7日来潮,6天干净,用纸不到3刀,余症状亦消失。
继服上方以巩固疗效。
按:患者二七之年,正值经期劳累致崩,二七肾气初盛,肾精未实,肾气未充,在此肾气不足之时,又劳伤冲任,致不能约束精血为崩。患者长期便溏、纳差,口中乏味,此中气不足,不能统血,脾肾俱虚,每经行,血海泛滥,有不能止遏之势,肾欲藏之而不能,脾欲摄之而不得。长期大量出血,精血亦随之耗损,治宜滋肾健脾,固肾止血。滋肾以养精血固肾为主,健脾以助脾气引血归经为法,方中熟地、枸杞子、阿胶、山萸肉滋养肾精,其中山萸肉、芡实又可固肾涩精,山萸肉性味酸涩偏温,古人谓其“强阴益精,安五脏,收涩之中兼具条达之性,补益奇经而有止血之功”。芡实味甘涩,能补脾胃,滋任脉,补中兼涩,以土滋肾固肾以安血之室;方中党参、白术、山药健脾益气,其中白术、山药同用,白术甘温偏燥,补脾益气,山药甘平柔润多汁,益脾阴,二药同用,燥润并施;再者熟地与党参同用,党参有健运之功,熟地禀静顺之德,一阴一阳相为表里,一形一气互主生成,此乃益气之中不忘扶阴之法;又黑姜炭温中止血,引血归经,补中而兼收敛之功;荆芥炭引血归经,其用在于止血而无寒冻之苦;全方以脾肾为主,扶脾以益血之源,补肾以固经之本,治脾重在以甘味药补脾气,以益生发之气,盖甘能生血,甘能养脏,治肾以滋肾精为主,兼顾精血,养精血以培补耗损,固精血以防无度之耗泄。
血崩伴眩晕1例
周某,女,41岁,初诊:1984年11月18日。
素月经量多,近三个月来,月经量特多,每用纸4~5刀,经行7~8天干净,经行腹痛,色红有块,经期提前一周左右,经净后白带中夹有血丝。经行时常发眩晕,甚时不能起床,睁眼视物旋转,恶心呕吐,耳鸣;平素口干苦,小便黄,大便干,纳差乏力,入睡多梦,牙龈出血,烦躁、心慌、多汗,末次月经1984年10月30日。西医诊断:梅尼埃病、继发性贫血。曾用中药治疗,多用化痰之药,无效,舌质淡,苔黄微厚欠润,脉细数滑。
此肝肾不足,肝阳偏旺,肝旺侮脾。治宜滋肾潜阳,健脾止呕。
竹茹10g 白术10g 山药15g 甘草4.5g 橘红9g 白芍20g 枸杞子15g 石决明30g 熟地20g 茯苓12g 旱莲草24g 阿胶15g
二诊:1984年12月5日。
服药后月经于11月25日来潮,量减少,仅用纸3刀+,经行6天干净,腹痛减轻,眩晕发作次数减少,余症均明显减轻,仍纳差,舌淡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去阿胶。
三诊:1985年2月25日。
服药后月经基本正常,眩晕近一月未发,纳食增加,余无特殊不适,舌红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以善其后。
按:月经量多伴眩晕,内科就诊以其苔厚、呕吐、脉滑数均以痰热论治,治痰之药燥而伤阴,病情有增无减。黄老观其月经量多,肝血肾精受伐,肝体柔性刚,赖水以养,今失其阴柔则刚燥之性易萌,肝乃风木之脏,风性喜动,木性外发,又内寄相火,一有激动龙雷不潜,相火外腾,上扰清空而眩晕、耳鸣;肝旺侮脾,纳差,使胃气上冲则呕吐;肝阳化火故口干苦,小便黄,大便干结,热扰血室,疏泄无度,则月经量多。若是痰浊为患,大便应溏,且服化痰药后病情应缓解,今病情加重,可见非痰所致。实肝肾不足,肝阳上扰,肝旺侮脾。正如叶天士说:“水亏不能涵木,厥阴化风鼓动,烦劳阳外,病甚自发矣。”虽眩晕、呕吐、耳鸣表现在上,实病根在下,长期精血耗损所致,伐其下者,枯其上也。治宜滋养肝肾为主,方用熟地、枸杞子、旱莲草滋肾壮水,滋其苗者灌其根也,重用白芍、阿胶养肝血、柔肝敛阴,阿胶、旱莲草又可止血崩,此肝肾同滋,抑木务先滋水,阴平则阳自秘,平肝重在养血,血充则肝自平。白术、山药、茯苓、甘草健脾,木横土衰,培中可效;用竹茹清肝热,利小便,又可降胃中上逆之气,使之下行;石决明平肝潜阳,正如叶天士所曰:“凡肝阳有余,必以介类潜之”,收摄横逆龙相之火。全方肝脾肾三脏同治,滋肾之液以清热,缓肝之急以熄风,培土之虚以生精血,扶阴分之不足为主,抑阳分之有余为辅,不治月经而月经自调。从此例可见,治此等虚风暗动之症,其风非发散可解,其火非沉寒可清,重在滋补,以培其本。正如《景岳全书》眩晕一证,虚者居其八九,而兼火兼痰者,不过十之一二耳。
血崩伴阴道流水1例
李某某,女,34岁,初诊:1984年11月27日。
月经提前量多,伴阴道流水两年余。
1982年生小孩,产后大出血,以后月经逐月增多,质稀,有小血块,伴腹隐痛,每次用纸6~7刀,经行8~10天干净,每20余天一潮,每经行前后阴道流黄水,量多,需垫纸。伴腰疼痛,面肿,失眠多梦,纳差,面色[插图]白,二便正常。今年6月份作B超提示“左侧附件囊性包块”。末次月经11月14日。舌淡,苔白,脉细软。
近年来患者一直服中药治疗,观前所用方均清热止血或清利下焦湿热之剂。
此脾肾不足,冲任受损。治宜温肾健脾,益气养血。
党参15g 黄芪15g 白术15g 山药15g 当归10g 白芍12g 巴戟天10g 菟丝子12g 枸杞子12g 鹿角霜15g 熟地20g 补骨脂10g 荆芥炭4.5g 生甘草6g
二诊:1984年12月15日。
服药后阴道流黄水已净,纳差,腰痛减轻,精神好转,这次月经12月9日来潮,量较前减少,用纸3刀余,今经行第6天,量极少,将净,余无不适,舌淡红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。
随诊半年余,均随上方加减,现月经已基本恢复正常,阴道已不流水,余证均减轻。
按:月经量多伴阴道流水,起病于生产大出血后,可见冲任受损,气血俱伤。精血外泄,阳气亦因之势微。人言:“血者阴类,得热则行,遇寒则凝。”亦有因阳气虚,统摄无权而致崩者。盖气为血帅,气虚则血无制而暴下,血去而气更虚,气虚而血尤脱。况患者伴阴道流水,并见纳差、面肿、经质清稀,畏冷腰痛,夜尿多,其脾肾阳虚之象若是。脾主统摄司运化,肾主封藏司水液,脾阳不振,运化无权,统摄失司;肾阳虚衰,封藏失职,水液气化失常。且肾乃水火之宅,火潜水中,真水不足对上不能温煦脾阳,对下不能摄精制水。经行前后,精血下注外泄之时,脾肾之阳益虚,统摄制水两失所司,而致精血外泄,精微不化,制水无权,发为崩中和经前后泄水证。阴道流水,世人一见色黄,均以湿热之证。崩中起于大出血后,且伴月经先期,以为阴虚热迫血行,观前面用药多以湿热论治,既伤阴血,又损阳气。譬犹冰冻之地,又遭寒霜,非但无益,反受其害,正如薛立斋所言:“苛用寒凉止血之药,复伤脾胃,反不能摄血归源,是速其危也。”既脾肾阳虚,就应温补脾肾,但毕竟起病于大出血后,又经行量多如崩,阴道流水,精血为之大伤,所以虽宜温,只宜温润,不宜温燥,否则愈耗精血。方中用党参、黄芪、白术健脾益气,俾血随气生,帅摄有主;巴戟天、补骨脂、鹿角霜温肾助阳,温而不燥,均肾家阳药中之驯良者,补骨脂又可强腰治其腰痛,鹿角霜软坚散结,治其附件包块;妙在重用熟地滋肾,当归、白芍养血,枸杞子、菟丝温润添精。以上诸药合于温阳药中以求水中补火,阴中求阳,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。荆芥炭引血归经又可止阴道流水,少佐一味生甘草泻火解毒,因其毕竟阴道流水色黄。全方重在治脾肾,补脾胃以资血之源,养肾气以安血之室。用药冲和,忌用刚燥,其调经之法,不先治水,亦不惟治其血,而重在补气,气旺而血自生,气旺而湿自除,此治之妙也。
肾虚血崩(更年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)1例
王某某,女,48岁,初诊:1985年11月2日。
患者一贯月经量多,近一年月经紊乱,经期超前,甚至一月两潮,经量特多,淋漓不尽,经净后又赤白带下,带下量多,伴口鼻干燥、身燥,下肢尤甚,夜晚有时燥得不能入睡,经常耳鸣,大便一贯溏,平时稍吃滋腻即大便稀,舌质淡,苔薄,脉右沉细、左细数。多次服中药,均无明显疗效。观所用药均养阴清热之品。这次月经10月20日来潮,至今未净。
百合24g 山药20g 芡实15g 甘草6g 乌贼骨20g 贯众炭12g 荆芥炭4.5g 五味子4.5g 煅龙牡30g
二诊:1985年12月6日。
服药后上次月经11月5日干净,这次月经12月1日来潮,今日已有将净之势,用纸2刀,大便基本正常,烦躁、带下亦较前明显好转。舌质红,苔薄,脉细。
继服上方观察3个月,月经恢复正常。
按:患者年近五旬,冲任已衰,开合无制,是为漏下之证。其辨证看,身燥,口鼻干燥,可见有热;又大便溏泄亦甚,又非能以热概之,而有中阳不足之证。血海不宁,投之以凉,折其沸腾之势,但损伤脾之阳气,脾虚不能摄血归源,致经行淋漓不断,非属正治。纯补脾益气,忘却患者阴虚之证,不独无益,反增燥灼温热助动之嫌。因此治疗上宜阴阳兼顾,用药避其寒热偏颇。《妇人规》云:“若虚夹火者,所重在虚,当以养营安血为主”,养营重在补中焦,助气血生化之源。方中以山药、芡实、甘草补脾益气,不用党参、白术、炙甘草温燥动血,此补虚而无浮动之虑;安血以乌贼骨、五味子、煅龙牡固涩止血,此安血而无寒凉之苦;贯众炭止血又可清热解毒治赤白带下;荆芥炭引血归经又可止带,而无寒凉碍胃之弊;重用百合养心安神除烦。全方以补中固涩止血为主,补中避温燥,止血避寒凉,是治疗本病的用药特点,亦是治疗取效的根本原因。
崩漏治疗小结
黄老治疗崩漏,不离塞流、澄源、复旧三法,但也不泥于初塞流、中澄源、末复旧的步骤,而是将三法融为一体。出血期间塞流时不离澄源、复旧;非经期复旧中重在澄源以治其本。以上7例崩漏,其病因各异,治法亦截然不同。因于火者,即火盛动血,多因虚火所致,非实火可比,治宜清热止血,但清热不用苦寒折火,以免泻火而伤阴,而以养阴为主,阴足而火平,养阴又以滋肾为主,肾者水脏,五脏之阴皆归于此。止血不专于炭药,虽言血色红,见黑则止,但药物炒炭后,改变或降低了药性,有人滥用炭药致离经之血不能畅流,反招瘀血为害。黄老每多选用生地、旱莲草、白芍、枸杞子、山药、阿胶等味,血热者加赤芍,口渴者加麦冬,大便干结者加制首乌等。气虚者,阳虚而阴必走是也,亦可表现月经先期、量多如崩、继而口干便结等症,与血热妄行者实难分辨,但细细审之无热象可查,绝非火迫所致,而有脾虚之象,治宜健脾益气为主,佐以止血,如党参、黄芪、白术、山药、甘草等药,且益气之中,不忘护阴,必加养阴止血之品,如生熟地、旱莲草、阿胶等,其引血归经之荆芥炭、黑姜炭也每酌情选用。
瘀血致崩,虽不可止血,亦不可一见包块癥瘕,纯于大队破气破血之药,因其虽可化瘀,恐有增加血量之嫌,如临床多见的子宫肌瘤血崩,每选用能化能消之鳖甲、浙贝母、鹿角霜、生牡蛎等。逐瘀如扫,而止血如神,即便活血,亦选用活中寓止之三七末、炒蒲黄、藕节等,不失通因通用之意,此于一般治瘀血致崩亦有独到之处。少女血崩,则多从脾肾着手,此类病者,多因先天肾气不足或后天失于调理,如经期跑步、负重、劳累。少女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,在此肾气不足之时又加劳累伤肾伤脾,而致脾肾亏损,治疗往往选用生熟地、旱莲草、阿胶、山药、党参、白术、枸杞子等。总之导致崩漏的病因甚多,其治法各不相同,但终不离肝、脾、肾三脏,随其病因而治之。治疗崩漏还应注意:①血者阴类,得热则行,遇寒则凝,崩漏一症动之有余,静之不足,故治宜以静镇之,因而用药宜偏平凉,不可过用温药;即使气虚致崩,亦不可尽用甘温益气,以防温热助动。②肾者封藏之本,精之处也,又经本于肾,故崩漏多兼肾虚,在益气养阴或温肾补阳的同时,要加固肾摄精之品,才能阴充阳复,如五味子、芡实、生牡蛎等。③崩漏之时慎用淡渗利下之药,如茯苓等,虽能健脾,但淡渗利下,必致崩漏盈甚,临床用药又不可不知。